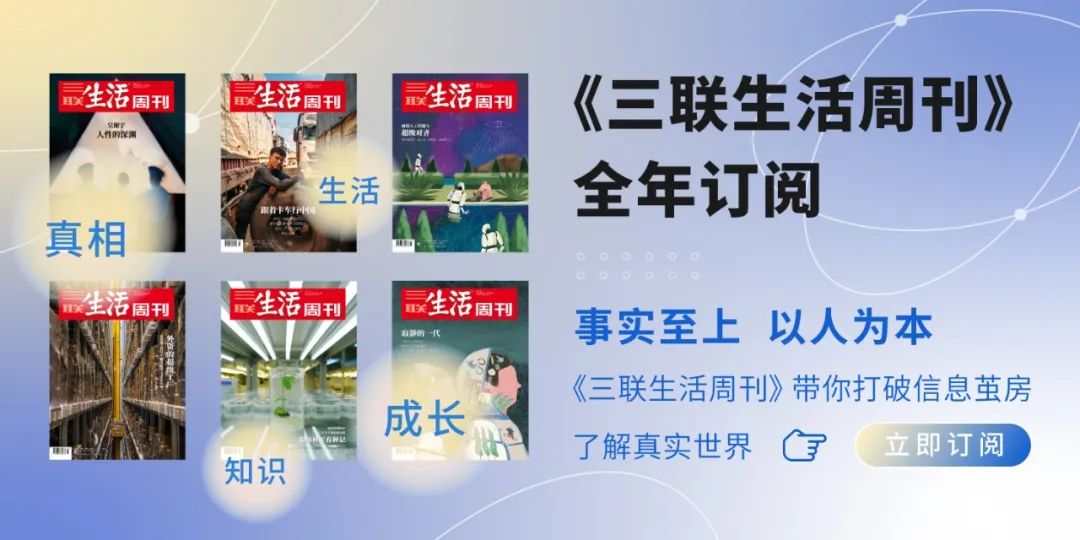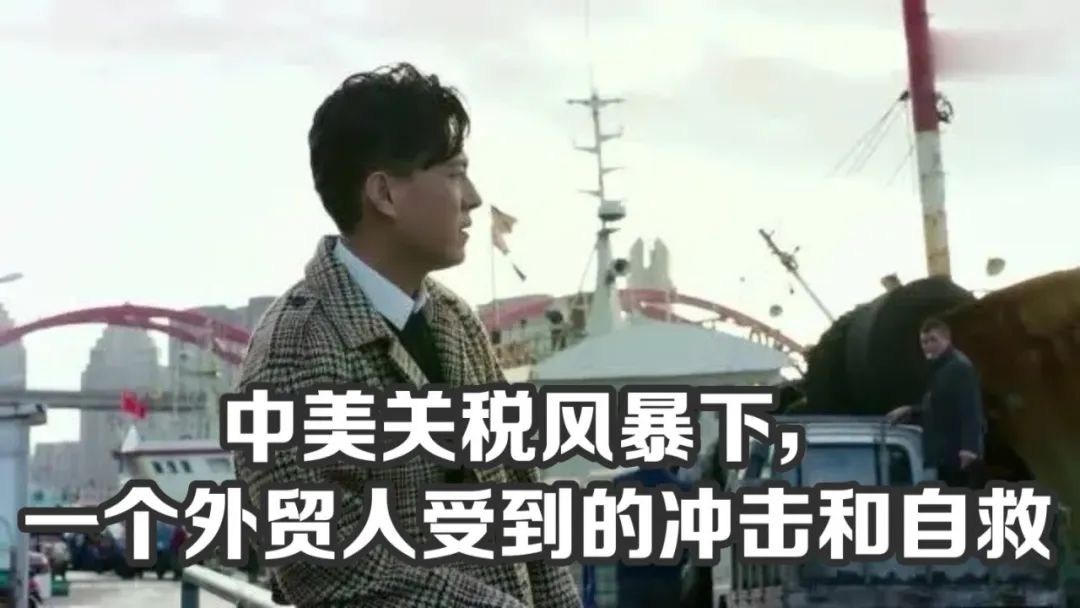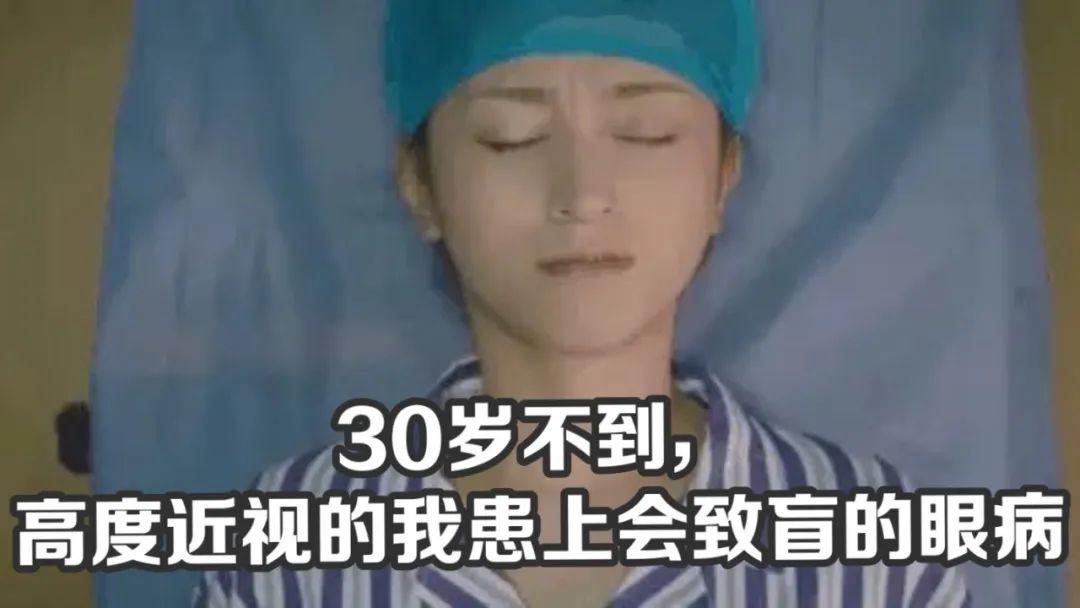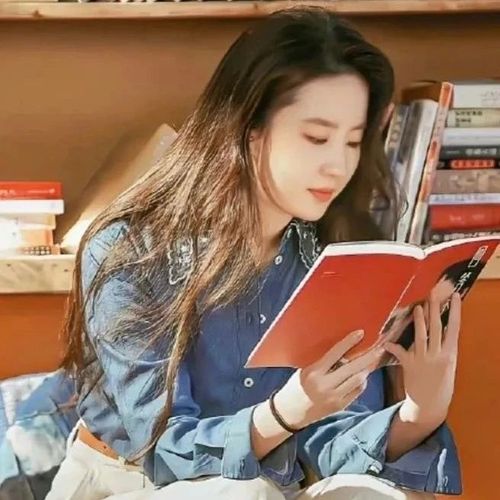困在评分系统里的餐饮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4-25·阅读时长28分钟
42人看过
某种程度上,正是大众点评构建的评分系统,重塑了餐饮业的底层逻辑。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开选题会,同事分享一件趣闻,说她一个朋友去川西团建,在那个山旮旯里吃了一家牦牛火锅店,老板不停地催他们在大众点评上写好评。那家店的位置有多偏?是在四川省阿坝自治州一个县的国道旁边。我问到这家店,上大众点评查看了一番,发现它的评论数多达1744条,其中差评数为0。
在一二线城市的餐厅消费,我们如今已习惯了服务员提出的送赠品写好评。
但这个例子还是让人有点小小震惊,同时也让我们想起,除了邀请好评,商家还鼓励我们从大众点评上购买套餐和代金券,这分明是使他们收益减少的行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大众点评这个平台创建二十多年,今天的餐饮商家有多在意它们的评分?而这些评分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家餐厅的生死?
这些好奇与疑惑触发了这个选题。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某种程度上,正是大众点评构建的评分系统,重塑了餐饮业的底层逻辑。
刘含山(化名)在老家宁波开了一家中式小酒馆,生意挺不错,当他在本地开的三家店都维持住了稳定的高人气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挺进上海。
上海是中国餐饮业的“高地”,消费高,竞争激烈,更新迭代也很快。听说刘含山这个勇敢的决定后,他的同行和朋友们纷纷向他提建议,总结下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是三个月没有起色,那百分之九十九是没希望了;二是花在大众点评上的预算一定要有。
刘含山从谏如流,2023年在上海开业第一家店时,前期预算一百多万,花了15%左右当“市场推广费”,也就是流量投入。这个钱怎么花?甚至不需要刘含山自己操心。店铺租完,装修工地刚围上围档,各种电话就打进来了,“不知道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打进来的电话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做线上点评相关的业务运营的,他们会举例说,大众点评上静安区餐饮热门榜第一名是他们做的,已经霸榜一年了。
也有大众点评app平台(以下简称“大众点评”)的业务员打进来,那时候,大众点评已经有了他的店铺页面。刘含山不知道是谁传上去的,但他后来知道,业务员们会“扫街”,哪里有即将开张的店铺,他们了如指掌,“相当于在森林里捕猎”。
店铺页面的初始状态相当粗糙,刘含山说,“只有一张牛头不对马嘴的照片,联系电话也是乱填的”。原则上,一个普通用户就可以为任意一家店铺上传图片,但哪张图片能作为店铺封面是随机的。作为商户,如果想按照自己的心意“装修”店铺、上传菜单、修改联系方式等,就需要下载“开店宝”app,上传营业执照认领自己在大众点评上的店,同时再花9800元的年费开通“商户通”。
这也是上海餐饮行业竞争激烈的一个侧面,因为其它有的城市,商家不付费就能获得这两项基础权限,或者需要付费,但金额低一些,比如宁波和杭州(餐饮商家)都是6800元一年。刘含山说宁波没有那么卷,他只花了6800元一年的基础费用。
作为去上海挑战的地方菜,交完年费,刘含山不敢怠慢,正式开张前,又花5万多与一个运营公司签了半年合同,对方承诺提供的服务包括,店面形象装修、图片和评分维护等等。但这只是基础费用,后续假如需要增加达人探店、高评级用户评价等等,要另外付费。
这些额外付费的内容,能换得的最诱人的东西就是流量。
在“开店宝”上,每家店铺都有一个“ROS门店等级”,共6个级别,从Lv.1到Lv.6。按照后台的测算,比如“上传至少15张官方相册图片”,就可以获得3分,帮助你从Lv.1升级到Lv.2,客流量增加268%。至于最高级Lv.6的商家,理论上能比Lv.1级获得增加9278%的流量。
餐饮行业资深从业者曹近海(化名)跟我打了个比方:“在大众点评上有流量和没流量的区别,相当于前网络时代,将餐馆开在车水马龙的闹市区和人迹罕至的深巷的区别”。
曹近海是杭州一家本地菜餐馆的老板,他在大众点评上架了套餐和代金券两项功能,目前门店等级已达到Lv.3。如果他还想升级到Lv.4(“预计门店流量+85%”),需要让店铺提升10分。如何得分?他告诉我,假如他再将套餐的平均折扣降到≤7折,与此同时,代金券满足≤9折,门店就能获得4分。“套餐”和“代金券”的核销达到一定金额或排名,也能获得相应的分数。总之,ROS这套等级制度总分为100分,Lv.6级至少需要90分,商家想获得这些分数,就需要投入真金白银,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这是曹近海开的第二家店,2024年底开业,上下两层,三百多平米,一层堂食,二层有五个包厢,光是装修就花去三百多万。第一家店他经营了六年多,是家80平米的小店。他曾信誓旦旦说“绝对不在大众点评上花一分钱”,开了新店之后就妥协了。在杭州,这个体量的餐厅都在做线上流量,如果你不做,那等于是——在戏院看戏,所有人都站起来了,只有你坐着。
 《欢乐颂》剧照
不过曹近海说,他不打算再晋级了,他觉得“它有点像毒品”。同样是旅游城市的重庆,有家连锁火锅店已经将每个门店都升到了最高级,俨然是一位资深玩家。火锅店的老板老温从业十多年,在他眼里,“现在哪有(餐馆)不做大众点评的”。
老温告诉我,他做过多个连锁火锅店,而且只做商圈店。商圈店的特点是,客人都是特地前来,一般来说,在出门之前,他们就已经做好决策,“不像社区店可以做复购,商圈店对大众点评依赖性很高,那是没办法的事儿”。这就意味着,能不能挤进商圈热门榜单前十,影响重大。大众点评上所有能开通的业务,他都开通了,他的目标就是进前十,能否进前十的影响因素相当复杂,但以老温的经验来说,上述这些投入都是必须的。
在上海餐饮界,大众点评分数4.5分以上的餐厅比比皆是,因此一个普遍的认知是,如果一个店铺低于4.3分,就很可能被消费者判定为“不值得去”。正是因为餐厅评分通货膨胀,2024年初,曾有过一波“年轻人报复性挤爆3.5分餐厅”的小潮流,算是一次抗议。但这远不足以妨碍高分餐厅更能获得流量的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大家去餐厅消费总被邀请写好评的原因。但理论上,这是违反平台规则的。id为“蒜瓣_”的小红书用户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叫“扑扑”的刨冰店,前一阵子搞活动,鼓励到店客人写评价,赠送一个冰淇淋球,按这位老板的说法,她跟店员强调了,要客人“客观真实的评价”,不是盲目好评。但活动过后,店铺还是被大众点评判定“干扰评价秩序”,“不展示星级7天”。不展示期间,顾客只能通过准确搜索店名,才能看到这家店,并且暂无星级。对个体商家来说,等于在大众点评上封店了。“蒜瓣_”在视频里说,现在,为了让评价显得“真实”,遇到特别喜欢扑扑的客人说要写5星好评,她会特地询问,能不能只写到4.5分。
“蒜瓣_”的吐槽视频下面,有近400条留言,大都是个体商户的共鸣。有人说,他们遇到过有客写了差评后,立马有人主动来联系,能删差评。在银川市开了名为“Aakery”面包房的老板留言说,“上次聊天的时候我们还是4.2分,随着服务和品质的不断提升,现在终于稳坐3.9分的黄金分数段了”。
《欢乐颂》剧照
不过曹近海说,他不打算再晋级了,他觉得“它有点像毒品”。同样是旅游城市的重庆,有家连锁火锅店已经将每个门店都升到了最高级,俨然是一位资深玩家。火锅店的老板老温从业十多年,在他眼里,“现在哪有(餐馆)不做大众点评的”。
老温告诉我,他做过多个连锁火锅店,而且只做商圈店。商圈店的特点是,客人都是特地前来,一般来说,在出门之前,他们就已经做好决策,“不像社区店可以做复购,商圈店对大众点评依赖性很高,那是没办法的事儿”。这就意味着,能不能挤进商圈热门榜单前十,影响重大。大众点评上所有能开通的业务,他都开通了,他的目标就是进前十,能否进前十的影响因素相当复杂,但以老温的经验来说,上述这些投入都是必须的。
在上海餐饮界,大众点评分数4.5分以上的餐厅比比皆是,因此一个普遍的认知是,如果一个店铺低于4.3分,就很可能被消费者判定为“不值得去”。正是因为餐厅评分通货膨胀,2024年初,曾有过一波“年轻人报复性挤爆3.5分餐厅”的小潮流,算是一次抗议。但这远不足以妨碍高分餐厅更能获得流量的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大家去餐厅消费总被邀请写好评的原因。但理论上,这是违反平台规则的。id为“蒜瓣_”的小红书用户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叫“扑扑”的刨冰店,前一阵子搞活动,鼓励到店客人写评价,赠送一个冰淇淋球,按这位老板的说法,她跟店员强调了,要客人“客观真实的评价”,不是盲目好评。但活动过后,店铺还是被大众点评判定“干扰评价秩序”,“不展示星级7天”。不展示期间,顾客只能通过准确搜索店名,才能看到这家店,并且暂无星级。对个体商家来说,等于在大众点评上封店了。“蒜瓣_”在视频里说,现在,为了让评价显得“真实”,遇到特别喜欢扑扑的客人说要写5星好评,她会特地询问,能不能只写到4.5分。
“蒜瓣_”的吐槽视频下面,有近400条留言,大都是个体商户的共鸣。有人说,他们遇到过有客写了差评后,立马有人主动来联系,能删差评。在银川市开了名为“Aakery”面包房的老板留言说,“上次聊天的时候我们还是4.2分,随着服务和品质的不断提升,现在终于稳坐3.9分的黄金分数段了”。
 《故乡,别来无恙》剧照
刘含山在上海的店采取的是订餐制,如今不但已经在上海存活下来,并且还开了两家店,而且客人还常常约不上,没有做大众点评不但活下来了,还活得很好。“不做大众点评”的结果就是,两家店分数徘徊在3.9~4.2之间。一个普通顾客也能看出来,这算是一个相当难看的评分。刘含山的店不依赖大众点评引流,但他看到差评,还是忍不住要去维护一下。
“一条差评干黄一家店”,这是很多餐饮人听说过的噩梦。假如你在小红书用关键词“大众点评+差评”搜索,能搜到几千条令商家胆颤心惊的笔记,其中有不少是运营公司发的,讲的都是这类故事。大家身边并没有这类实例,但差评的确会影响获客率。一位在重庆做万州烤鱼的老板告诉我,曾经有一次,他的店里被人打了批评口味的差评,他明显感觉到接下来一周的客流量显著下降,他不得不紧急上架了几个亏损套餐来争取客流。
一个餐饮从业者的普遍认知是,一条差评对评分的影响,大概需要20条好评去覆盖。不过这里面又有一个门道,即消费者的大众点评账号等级会影响评价的权重。小何是一个资深美食爱好者,热爱探店,热爱写评价,并在2018年晋级为大众点评V8用户。随后,她就被拉进了几个“运营群”,会有人在群里发布某某餐厅几人餐的免费试餐机会,代价是写好评,并且是图文并茂的好评。她说,平常自己出去吃饭,碰到不满意的餐厅,她也很少会写差评,就是因为知道V8用户的差评可能给餐厅带去的困扰。
刘含山的店里,最近就有几个差评是因为抢不到用餐位置被打的。刘含山认为,他们都没来过,就要写差评,那就不合理。商家去申诉时,平台表示,如今对差评的审核权限已交给“大众评审”。
“大众评审”是我这次采访才听说的名词。我在大众点评找到它的入口,打算研究一番,没想到只花去不到一分钟,我就成了一名大众评审。加入后,平台共发给我六个案例,都是差评内容以及商家对此的申诉,随后,有两个选项摆在我面前。一是“适合展示”,意思是我认为差评有理,二是“不适合展示”,相当于判定它为“恶意差评”。选完之后,页面还会展示当前投票结果。
刘含山为了研究怎么样回应差评的说辞,也加入了大众评审。一段时间后评审下来,他的总结是,支持商家的比例很少有超过50%的,也就是说,大部分差评都会被展示出来。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跟我提到说,他们都为不合理差评申诉过,但极少成功。大众评审本来就是“消费者”,大家天然地会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这本身合情合理,但刘含山觉得,问题在于“恶意差评”往往也埋没在所有差评里,并没有纠错机制。因为一旦“大众评审”出了结果,再想申诉就没可能了。
重庆火锅连锁店的老板老温前不久被一位客人在大众点评和美团两个app上都打了0.5分,理由是卫生条件差。老温发现,这位客人拍的照片明显是盗用自别的客人,可能他本人完全没到店消费,他怀疑这是同行干的,但他没有证据。他只能把盗用照片的证据提交上去,有意思的是,他在两边提交了一模一样的申诉材料,大众点评app上的申诉通过了,但美团app上却没有。
既然个体商户对大众点评有如此多怨言,那么,能不能干脆不做?从大众点评app下架自己的店铺,是不是就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是:理论上不可以,除非你费上一番曲折的功夫。
宁波人颜小翔是三家咖啡店的老板。六年前,他开出了Tosan Coffee,只有七平方米,位于市中心,是典型的社区小店,做的也是老客生意。到今年2月,Tosan Coffee的第三家店开业,3月,一位客人在“饿了么”上下单后,跟颜小翔沟通,因为喝了咖啡,出现了心悸等状况。
颜小翔说,他不接受这个评价,假如这位客人可以举证,比如提供医学证明,表明身体的确出状况,或者工商部门查出咖啡豆的确有问题,那他是可以承认的,“但他不能空口白话说我的咖啡有问题”。他解释,就像每个人对酒精耐受度不一样,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不一样,喝酒后脸红心跳加快,是不是也要认为是酒有问题?作为开店那么多年,同款卖出几千杯的咖啡店老板来说,他无法接受这样一条评价挂在页面上。
因为拒绝退单和赔偿,这位客人于是在他新店的大众点评页面上写了一条0.5星的差评。而且,这是一位V8用户,店铺的总评分于是立刻往下掉了。他去找大众点评的客服申诉和协调,都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这条评价的评论权限也被这位客人关了。换句话说,进入Tosan Coffee页面的用户,不仅会看到这条差评,可能还会琢磨,为什么这个商家连回复和辩解一下的努力都不肯做。
《故乡,别来无恙》剧照
刘含山在上海的店采取的是订餐制,如今不但已经在上海存活下来,并且还开了两家店,而且客人还常常约不上,没有做大众点评不但活下来了,还活得很好。“不做大众点评”的结果就是,两家店分数徘徊在3.9~4.2之间。一个普通顾客也能看出来,这算是一个相当难看的评分。刘含山的店不依赖大众点评引流,但他看到差评,还是忍不住要去维护一下。
“一条差评干黄一家店”,这是很多餐饮人听说过的噩梦。假如你在小红书用关键词“大众点评+差评”搜索,能搜到几千条令商家胆颤心惊的笔记,其中有不少是运营公司发的,讲的都是这类故事。大家身边并没有这类实例,但差评的确会影响获客率。一位在重庆做万州烤鱼的老板告诉我,曾经有一次,他的店里被人打了批评口味的差评,他明显感觉到接下来一周的客流量显著下降,他不得不紧急上架了几个亏损套餐来争取客流。
一个餐饮从业者的普遍认知是,一条差评对评分的影响,大概需要20条好评去覆盖。不过这里面又有一个门道,即消费者的大众点评账号等级会影响评价的权重。小何是一个资深美食爱好者,热爱探店,热爱写评价,并在2018年晋级为大众点评V8用户。随后,她就被拉进了几个“运营群”,会有人在群里发布某某餐厅几人餐的免费试餐机会,代价是写好评,并且是图文并茂的好评。她说,平常自己出去吃饭,碰到不满意的餐厅,她也很少会写差评,就是因为知道V8用户的差评可能给餐厅带去的困扰。
刘含山的店里,最近就有几个差评是因为抢不到用餐位置被打的。刘含山认为,他们都没来过,就要写差评,那就不合理。商家去申诉时,平台表示,如今对差评的审核权限已交给“大众评审”。
“大众评审”是我这次采访才听说的名词。我在大众点评找到它的入口,打算研究一番,没想到只花去不到一分钟,我就成了一名大众评审。加入后,平台共发给我六个案例,都是差评内容以及商家对此的申诉,随后,有两个选项摆在我面前。一是“适合展示”,意思是我认为差评有理,二是“不适合展示”,相当于判定它为“恶意差评”。选完之后,页面还会展示当前投票结果。
刘含山为了研究怎么样回应差评的说辞,也加入了大众评审。一段时间后评审下来,他的总结是,支持商家的比例很少有超过50%的,也就是说,大部分差评都会被展示出来。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跟我提到说,他们都为不合理差评申诉过,但极少成功。大众评审本来就是“消费者”,大家天然地会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这本身合情合理,但刘含山觉得,问题在于“恶意差评”往往也埋没在所有差评里,并没有纠错机制。因为一旦“大众评审”出了结果,再想申诉就没可能了。
重庆火锅连锁店的老板老温前不久被一位客人在大众点评和美团两个app上都打了0.5分,理由是卫生条件差。老温发现,这位客人拍的照片明显是盗用自别的客人,可能他本人完全没到店消费,他怀疑这是同行干的,但他没有证据。他只能把盗用照片的证据提交上去,有意思的是,他在两边提交了一模一样的申诉材料,大众点评app上的申诉通过了,但美团app上却没有。
既然个体商户对大众点评有如此多怨言,那么,能不能干脆不做?从大众点评app下架自己的店铺,是不是就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是:理论上不可以,除非你费上一番曲折的功夫。
宁波人颜小翔是三家咖啡店的老板。六年前,他开出了Tosan Coffee,只有七平方米,位于市中心,是典型的社区小店,做的也是老客生意。到今年2月,Tosan Coffee的第三家店开业,3月,一位客人在“饿了么”上下单后,跟颜小翔沟通,因为喝了咖啡,出现了心悸等状况。
颜小翔说,他不接受这个评价,假如这位客人可以举证,比如提供医学证明,表明身体的确出状况,或者工商部门查出咖啡豆的确有问题,那他是可以承认的,“但他不能空口白话说我的咖啡有问题”。他解释,就像每个人对酒精耐受度不一样,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不一样,喝酒后脸红心跳加快,是不是也要认为是酒有问题?作为开店那么多年,同款卖出几千杯的咖啡店老板来说,他无法接受这样一条评价挂在页面上。
因为拒绝退单和赔偿,这位客人于是在他新店的大众点评页面上写了一条0.5星的差评。而且,这是一位V8用户,店铺的总评分于是立刻往下掉了。他去找大众点评的客服申诉和协调,都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这条评价的评论权限也被这位客人关了。换句话说,进入Tosan Coffee页面的用户,不仅会看到这条差评,可能还会琢磨,为什么这个商家连回复和辩解一下的努力都不肯做。
 《三十而已》剧照
在这个过程中,颜小翔的感受是“非常弱势”,连辩解空间都没有。颜小翔决定,既然如此,那就下架店铺。
随后他发现,作为店铺的经营者,他并没有下架自己店铺的权限。大众点评的客服告诉他,“我们不能下架您的店铺,除非您的店铺停业了,它就会慢慢下架掉”。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平台并不负责上架或下架某一家店铺,他们只是“抓取信息”。
但颜小翔不愿意就此放弃。他打了上海市的消费者协会热线和市长热线,最后不知道是哪个电话起了作用,上海市一位知识产权局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前后跟他沟通了一周,最后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下架前,这位工作人员还提醒他,下架以后,再上架就很困难了,请他想好。颜小翔告诉我说,他当然考虑过得失,一旦下架,一定会有一些麻烦。
三家店铺都从平台上下架后,颜小翔频繁接到老客人的咨询电话和微信,有的问他要地址,有的问他是不是停业了,当然还有潜在失去的客流。不过,与换来的清静相比,这是他愿意承担的后果。
一条差评或许并不能干黄一家店,但这个案例中的这条差评,的确直接导致了这家咖啡店从“大众点评”平台上消失。
听说我采访了一位成功下架店铺的老板后,刘含山第一反应是,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他们也做过设想,要是不在这个平台上出现,做起生意来会不会麻烦更少点。但Tosan Coffee的“成功”经验,或许很难复制。颜小翔把这个经验发在小红书上之后,有不少人私信问他方法,他说他实际上并不认为下架店铺适合所有人,他的底气在于,他的咖啡店是社区店,而且多年以来累积了很多熟客。
《三十而已》剧照
在这个过程中,颜小翔的感受是“非常弱势”,连辩解空间都没有。颜小翔决定,既然如此,那就下架店铺。
随后他发现,作为店铺的经营者,他并没有下架自己店铺的权限。大众点评的客服告诉他,“我们不能下架您的店铺,除非您的店铺停业了,它就会慢慢下架掉”。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平台并不负责上架或下架某一家店铺,他们只是“抓取信息”。
但颜小翔不愿意就此放弃。他打了上海市的消费者协会热线和市长热线,最后不知道是哪个电话起了作用,上海市一位知识产权局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前后跟他沟通了一周,最后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下架前,这位工作人员还提醒他,下架以后,再上架就很困难了,请他想好。颜小翔告诉我说,他当然考虑过得失,一旦下架,一定会有一些麻烦。
三家店铺都从平台上下架后,颜小翔频繁接到老客人的咨询电话和微信,有的问他要地址,有的问他是不是停业了,当然还有潜在失去的客流。不过,与换来的清静相比,这是他愿意承担的后果。
一条差评或许并不能干黄一家店,但这个案例中的这条差评,的确直接导致了这家咖啡店从“大众点评”平台上消失。
听说我采访了一位成功下架店铺的老板后,刘含山第一反应是,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他们也做过设想,要是不在这个平台上出现,做起生意来会不会麻烦更少点。但Tosan Coffee的“成功”经验,或许很难复制。颜小翔把这个经验发在小红书上之后,有不少人私信问他方法,他说他实际上并不认为下架店铺适合所有人,他的底气在于,他的咖啡店是社区店,而且多年以来累积了很多熟客。
 《无名》剧照
《无名》剧照
假如不逃离,而是全面拥抱大众点评呢?结果未必会令人满意。苏州的老徐饭店(化名)是一家开业二十多年的老店,以老客和熟客为主,而苏州作为老牌旅游胜地,游客数量也不少,老徐饭店口碑一直不错。去年以来,因为经济环境整体并不乐观,他们这样的老店生意也有所下滑,有朋友建议他们去大众点评上获得流量。但是线上曝光增加的同时,差评也来了。老板告诉我说,他们的感受是委屈和气愤,比如最让他无法接受的一个评价是说排骨不新鲜,像他们这样的老店都是靠口碑做下来的,食材不新鲜早就倒闭了,但是即便提供了进货证据,申诉也以失败告终。
广东中山的梁老板告诉我,她从2015年开始做餐饮,从四张桌子的小店做起,生意逐渐壮大,三年前,她孤注一掷,投入二百多万开了一家400平的大餐厅。团购、套餐等这些线上获客手段全都用上了,每做一单都要亏十几块钱,最后撑不下去转让之前,她苦苦坚持了一年多。
就像在戏院里看戏,当前面有人站起来的时候,你也不得不站起来,而所有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就等于谁都没站起来。一些认为做大众点评没有出路的商家,开始寻找其它流量。
直到2023年,贵州人Sunny还是餐饮小白,她和闺蜜二人原来是美发行业从业者,去年,二人决定做餐饮。她们本来的打算是,就算一个月赚5000块,也比上班强。她们瞄准的是螺蛳粉,假如事先请教过一些餐饮专业人士,她们很可能会被告知,“螺狮粉赛道已经是一片红海,做不出来了”,偏偏就是这一对比较懵懂的姐妹,做到第四个月,就开了三家店。她们的方法就是在小红书和抖音上做账号。Sunny说,她们成功的原因,除了每天现熬汤汁(而不是像大多数螺蛳粉那样是预制菜)外,最重要的可能是踩中了某个赛道——做餐饮的愿意出镜的本来也少,而她们姐妹又长得挺漂亮,两个漂亮姑娘每天起早贪黑干餐饮,“美强惨”形象既新鲜又有张力,这种反差感帮助她们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了很多流量。
至于大众点评,为什么不做?Sunny说,既然都得为流量投预算,与其把钱花在大众点评上,给平台增加流量,不如把钱花在自己做账号上。事实上,这个策略蛮成功的,因为螺蛳粉店无法继续扩张,关掉之后,她们又转头开起了饺子馆。假如流量来源是大众点评,开了新店,她们就得从头来过,而小红书同一个账号,是同一对漂亮老板娘,依照同一套逻辑,饺子馆的生意依然相当不错。
 《玫瑰的故事》剧照
Sunny说假如她们继续做美发店,很可能没办法转战小红书,因为很少有人会上小红书或抖音搜索“按摩理发去哪里”。越依赖大众点评,店铺评分给人的压力越大,当时每年在平台上投入的钱相当可观,“无非就是刷好评,打卡签到这些玩法”。也正是因为做美发店的经历,处理差评的体验让她心有余悸。
不过,逃离了一个平台,进入的或许是另一个看不见的系统。流量与算法已经吞噬了传统餐饮行业的逻辑,过去开饭馆的守店模式已经被互联网消灭。夸张一点说,新开的饭馆几乎只有三个月生命周期,不太可能会存在开上一两年后生意慢慢好起来的故事了。刘含山说,他们进上海之前,还有所谓的餐饮顾问给他们提过建议,说一定要有一两道专为争夺流量设计的单品。就像现在流行的抹茶流心、龙井豆浆、蜂巢米酒,大多数都是好看不好吃,很可能也跟餐厅本身的风味不搭配。以及,餐品的照片怎么拍,菜单怎么设计,甚至菜品的名字怎么起,都要遵循流量的逻辑。
假如一个平台拥有垄断性地位,成为规则制定者,商家按照这套规则去执行的结果是自我压榨,以利润换生存,在流量和规则的夹缝中挣扎,恐怕最终也会反噬到消费者,就比如那些流量追捧中同质化的菜品,和明明味道不错却不被看见的餐馆。
《玫瑰的故事》剧照
Sunny说假如她们继续做美发店,很可能没办法转战小红书,因为很少有人会上小红书或抖音搜索“按摩理发去哪里”。越依赖大众点评,店铺评分给人的压力越大,当时每年在平台上投入的钱相当可观,“无非就是刷好评,打卡签到这些玩法”。也正是因为做美发店的经历,处理差评的体验让她心有余悸。
不过,逃离了一个平台,进入的或许是另一个看不见的系统。流量与算法已经吞噬了传统餐饮行业的逻辑,过去开饭馆的守店模式已经被互联网消灭。夸张一点说,新开的饭馆几乎只有三个月生命周期,不太可能会存在开上一两年后生意慢慢好起来的故事了。刘含山说,他们进上海之前,还有所谓的餐饮顾问给他们提过建议,说一定要有一两道专为争夺流量设计的单品。就像现在流行的抹茶流心、龙井豆浆、蜂巢米酒,大多数都是好看不好吃,很可能也跟餐厅本身的风味不搭配。以及,餐品的照片怎么拍,菜单怎么设计,甚至菜品的名字怎么起,都要遵循流量的逻辑。
假如一个平台拥有垄断性地位,成为规则制定者,商家按照这套规则去执行的结果是自我压榨,以利润换生存,在流量和规则的夹缝中挣扎,恐怕最终也会反噬到消费者,就比如那些流量追捧中同质化的菜品,和明明味道不错却不被看见的餐馆。
排版:初初 / 审核:小风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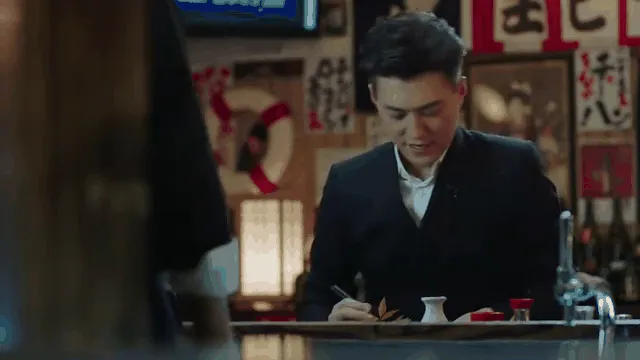

 《欢乐颂》剧照
《欢乐颂》剧照
 《故乡,别来无恙》剧照
《故乡,别来无恙》剧照


 《三十而已》剧照
《三十而已》剧照
 《无名》剧照
《无名》剧照 《玫瑰的故事》剧照
《玫瑰的故事》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