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少年在“矫正学校”死亡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5-10·阅读时长29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死亡
3月22日下午6点,张梅赶到医院时,儿子的遗体已经被白色的被单蒙住。拉开被单,本就瘦弱的儿子已经瘦得脱相,脸颊凹陷,腹部可以清晰地看到根根肋骨。他的四肢、腰部、胸口遍布青紫色的伤痕,腰部和左耳后各有一处硬币大小的伤口,已经结痂。“他的背部还有大片长条形伤痕,屁股一边结痂,一边血肉模糊。”一位接近周家的知情人梁军告诉本刊。
面对着伤痕累累的儿子,张梅濒临崩溃,已经不知道哭泣。梁军告诉本刊,尸检结果显示孩子全身并无致命伤,致死原因是“挤压综合征”。这是一种因肌肉长时间受到挤压,出现的以肢体肿胀、肢体坏死、高钾血症、肌红蛋白尿以及急性肾损伤为特点的一组临床综合征。自然灾害如地震、泥石流或者长期殴打等,均可导致该症状。梁军说,警方并未明确告知孩子死因,但提到有5名教官和多名学生被刑拘。

出事前,张梅和丈夫最后一次见儿子是在十天前,在派出所。当时周希军因为偷盗被抓,警方提出要将其送到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两人看着儿子,他穿着白色羽绒服,低着头不说话,张梅和丈夫在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之后,14岁的周希军被送到了株洲市启航辅导学校(以下简称“启航学校”)。这是一所民办专门学校,由株洲市教育局批准成立,主要面向12-17岁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治。梁军告诉本刊,进入学校后,周希军的父母不能跟儿子直接联系,他们会隔1-2天向心理老师询问儿子的情况,每次得到的回复均是情况良好。
张梅难以想象,儿子周希军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周希军入校时,同样因盗窃进入启航学校的魏薇,已经在里面待了五个多月。一开始,魏薇只是对周希军有些印象——入学三四天,他就被公开体罚。启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每天会在操场一起训练,这是他们在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魏薇记得那天,两名较早入校的老生各自抓住周希军的一只手,拖着仰面朝天的周希军,在100米长的操场上走了几个来回。
这种体罚在学校里并不罕见,训练态度不好、偷懒或者是不小心掉队,都有可能被教官惩罚。但之后频繁被殴打让魏薇记住了周希军。两天后的一节体育课上,魏薇看到,在礼堂门口,学校总教官王教官指着鼻子骂周希军“摆烂”。随后周希军的带班教官李教官冲上前去,拿着木质戒尺朝他身上打了十来下。戒尺约一条手臂长,两三根指头粗,上面刻着《弟子规》的片段。还有一次,学生们在礼堂看电影,魏薇看到其他人都坐着,只有周希军被要求蹲着,有两个老生看着他。他动了一下,两人就会打他。
在周希军入校的第10天,魏薇开始意识到不对劲。3月21日上午训练,周希军是被两名老生搀扶着来的,他那时双腿已经站不稳,脸瘦得皮包骨,嘴唇微微发白,“看起来像流浪几天的人”。教官跟他讲话,他张张嘴,但只能发出“啊啊啊”的声音,说不出话。中午吃饭时,两名老生架着周希军坐到座位上,他双手拿不稳筷子,坐一会就倒在地上,喂他喝水,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好像全身骨头都没力气。”
 《罪途》剧照
《罪途》剧照
3月22日,周希军缺席了全天的训练。到了傍晚5点,在食堂门口站军姿的魏薇看到,几名教官背着他从寝室出来,匆匆穿过操场,往门口方向走去。一名教官后来告诉学生,周希军连续被打几天后,有教官提出送他去医院,但学校不重视,直到那天傍晚5点,他们看到周希军气喘不上来,才把他送进医院,但一切都太晚了。
紧闭的红门
从株洲市区出发,一路经过起伏的红土坡,宽阔的河流,再走几公里颠簸破碎的山路,才能到达位于株洲市天元区的株木村。启航学校坐落于村庄里偏僻的一角,左边是一片小竹林。这所学校创办于2024年,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均被刷成红色,围墙内还有一圈5米高的铁皮遮挡,部分围墙上面挂着三角形的铁刺网,墙内传来拍打篮球的声音。周希军出事后,学校依旧正常运行。

株洲市启航辅导学校(陈银霞 摄)
回忆起启航,15岁的王子韬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那扇紧闭的大红门。王子韬去年11月因持刀斗殴被抓,随后被警察送入启航学校。王子韬说,大红门后,迎面是一道高墙,从墙左侧开的小门进去,才算进入了学校内部:中间是一个大操场,是学生平常的训练场地,操场左侧有一个凉亭和礼堂,右侧是食堂、厕所和办公楼,正前方是两栋楼,楼下寝室,楼上教室。校内到处都是监控,窗户均用铁栅栏封死,寝室门从外面锁住,上了3把锁。晚上还有教官陪寝,“很压抑。”
魏薇告诉本刊,启航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株洲本地,分为警送生和家送生。根据相关规定,警送生主要为因年龄原因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和检察机关决定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魏薇提到,启航的警送生由政府承担学费,矫正时间为3或6个月;家送生主要为存在不良行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法有效管教,需要求助专门学校的未成年学生,每月学费7000元。在魏薇的印象里,启航学校里九成以上学生为警送生,他们多数因盗窃被抓,少数斗殴。
魏薇说,学校有学生100余人、10名教官、1名心理老师、3-6名实习心理老师,以及几个文化课老师。平常主要课程是训练,包含蛙跳、俯卧撑、跑步、做操、打拳等。魏薇在学校的日子里,学生早上6点打起床铃,起床后整理内务,7点半集合早训,8点吃早饭。上午和下午均为训练。下午5点晚饭,饭后晚训或者看电影——看电影时也不能放松,得坐得笔直。今年三月中下旬开始,学校才零星开了几节文化课。
与王子韬感受到的压抑不同,作为较早入校的学生,魏薇对学校和教官印象不错,甚至感叹学校伙食好,在学校里胖了10斤。魏薇回忆,去年9月开学时,学生只有3人,教官有6人,训练时教官严格但不乏耐心,一遍遍教他们训练动作。教官多当过兵,有的还在针对叛逆学生开设的特训营待过。休息时,教官“跟我们像兄弟一样相处,给我们买冰红茶、可乐,陪我们跑操、打篮球,没有教官打人。”
在学生的记忆里,教官开始打人,是在去年11月。那正是王子韬入校的时期,当时学校的学生已经有22个,教官也增加了两名。“学生多了,又有不听话的,教官就没那么有精力和耐心。”王子韬告诉本刊,入校第一晚,他被要求做了1000个俯卧撑和上下蹲,一直做到凌晨1点。第六晚,晚上就寝时,因不小心笑了一声,王子韬被拽下床,总教官拿戒尺在他屁股上打了重重十几板,五名教官摁住他,“像摁鱼一样”。四个室友则站军姿列队在旁边看着。

去年12月底,六名学生翻墙逃跑。为了加强管理,老生陆续被任命为班长,辅助教官管理。训练时,教官会安排新生穿插在老生中间,老生监督新生。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一种隐形的权力格局就此形成:教官、班长、老生在权力的顶端,中间是家送生,底层是新生。班长通常由与教官关系好、训练能力强且待的时间久的老生担任。进入学校最早的魏薇在去年10月成了班长。她说,新生若想跟教官拉好关系,首先得跟班长处好。在学校里,魏薇身旁总围着一群人,甚至有专人为她提水杯。魏薇说,教官曾暗示过要对家送生好些,他们是学校盈利的一大来源。
迅速增加的学校
在魏薇的记忆里,启航学校的学生开始参与到殴打中,是从今年2月开始的。当时有个班级提拔了一个班长,对方“很狠”,训练时,学生手指没有对齐裤缝,他会当着教官的面,几个巴掌扇过去。这种暴力的管理手段,效果看起来十分明显。一周左右,这个班级学生们队列整齐,原本揉成一团丢在地上的被子,也被叠成豆腐块,甚至班级里偷烟的问题也不再发生。
“专门学校殴打问题的存在,与近五年专门学校扩张过快,对专门学校监督机制不完善,存在一定的关联。”中国犯罪学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苏明月从2005年开始研究专门学校。她告诉本刊,专门学校的前身是工读学校,工读学校设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面向有轻微违法的未成年人,采取半强制入学方式;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工读学校”写入法条,确定其为对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的方式。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唐稷尧长期致力于刑法学、少年法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告诉本刊,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工读学校的招生范围逐渐扩大,一些具有学校难以管教的青春期越轨行为(比如逃学、抽烟、喝酒、早恋、网瘾等)的未成年人也被纳入了招生对象,工读学校的入学方式也改为自愿申请入学。“绝大部分家长都不愿意把小孩送到工读学校,到本世纪初,工读学校因为招不到人,萎缩了。”为了消除社会的误解,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和2012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均将条文内涉及“工读学校”的部分,改名为“专门学校”。根据教育部2010年12月29日公布的《工读学校基本情况》数据,低谷时,2009年全国专门学校数量仅72所。
唐稷尧说,专门学校数量的增长与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2023年,最高检公布的信息提到,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趋多元,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增长,且呈现低龄化趋势。2018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32.7万人,年均上升7.7%;其中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2018年4600多人上升至2022年8700多人,年均上升16.7%。唐稷尧说,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除了少数几个法定的刑事不法行为类型之外,他们所实施的大部分不法行为都不构成犯罪,无法予以刑罚处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也难以对其处以拘留等行政处罚。如将这些孩子不加实际干预地放任于社会中,一方面可能对社会存在危险性因素,另一方面,则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从保护这些未成年人的角度来说也是不利的。
为此,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对专门教育的定位和专门学校的建设、管理、运行及保障机制作出规定。2021年开始正式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再次明确了专门学校的定位,即对未成年人开展专门教育的场所,专门教育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一样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未成年人具有实施法律所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情形,除了原来的“申请入学”方式之外,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还可以直接依法决定将其送进专门学校。唐稷尧说,这之后出现了一波改建、扩建和新建专门学校的潮流。教育部2023年底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119所专门学校,在校生8109人。到2024年7月,专门学校数量增至230所,翻了一倍。

株洲市教育局官网显示,2024年1月22日,株洲启航被准予“办学”
但快速建校背后,设施、师资和监管机制尚未完善。南方某省会城市一位公办专门学校的教官告诉本刊,他们学校1个教官只带2名学生,教官均从一线民警抽取。他们不允许殴打,而是采用实地走访学生的学校、家庭、派出所,批改学生心理日记等柔性方式教育。但苏明月看到,近几年随着社会需求的上升,政府在部分地区无法完全满足特殊教育需求,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逐渐进入这一领域。一些民办学校追求盈利的目标,可能导致它们在教育质量和管理上有所妥协。
具体到启航,教官与学生比例为1:10,教官多数是20多岁的退伍军人,大多缺乏教育经验。正式的心理老师只有一位,魏薇说,几位实习心理老师才19岁,是一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复杂的生源结构,也让老师的神经紧绷。王雪曾在湖南某民办专门学校担任心理老师。她告诉本刊,她感受到学生普遍缺爱,最初她是抱着关爱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但学生常常在背后骂她,有次还开黄腔,“我感觉自己也需要心理辅导”。王雪多次提到,她“无法接受”这些学生曾经厌学、早恋、怀孕甚至挑过别人脚筋,“稍微处理不好,就会惹祸上身。”负面情绪不断积压,她最终选择辞职。魏薇说,半年时间内,启航学校一开始的6名教官,走了4位。
苏明月提到,2021年收容教养制度被废止后,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改由专门学校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如何将他们与专门学校里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分类有效地进行教育矫治,避免交叉感染,是目前专门学校面临的一大挑战。唐稷尧告诉本刊,专门学校一方面要对孩子的不良行为进行矫正,对他人格的成长进行干预,一方面要促使他完成义务教育基本学业,同时还要给予他一定的职业教育。但关于如何开展专门教育,现行法律制度尚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各个地方操作方式不同,大都处于摸索阶段。“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专门教育在实施中具有一定的约束性甚至惩戒性。通过适当的约束和惩戒,可以矫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让他们明白犯了错误会面临不利的后果,需要承担责任,以帮助其建立起责任感。但惩戒又必须选择适当的方式(如一定期限的禁闭),并需要一定的限度,尤其是不能够使用殴打等体罚方式,如果用体罚,实际上就涉及侵犯未成年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越轨少年
在株洲市醴陵市,浦口镇能称得上是发达的乡镇。依靠烟花和陶瓷产业,小镇发展得像个小县城,繁华的十字街上,密布着多家零食店、槟榔店、奶茶店和麻将馆,2家台球厅和4家KTV均对未成年人开放。其中一家台球厅里放着两台老虎机,十几个男人守在一旁,往里面塞二三十元的纸币。地上丢满烟蒂,几个未成年人在旁边打球。

浦口镇街上的台球厅,很多未成年人在打台球(陈银霞 摄)
走在街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坚决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我的青春我做主,莫让毒品来支配”“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路边的电线杆上,也张贴着多张文武学校的招牌,用白色粗体字写着专门矫正“调皮网瘾孩子”。广告一路张贴到了浦口村。

浦口镇路边的电线杆上,张贴着多张特训学校的招牌(陈银霞 摄)
周希军的父母四十岁左右。他们的同村好友刘霞告诉本刊,张梅夫妇原先在广东打工,2010年村里的大型烟花厂开业后,夫妇俩便在烟花厂上班。刘霞说,张梅夫妇是村里的勤快人,繁忙时他们能连续通宵四五个晚上,孩子因此一直交给公婆带。但老两口很难管住孩子,奶奶出去来玩牌时,周希军常常坐在旁边看手机,不给手机就掀麻将。奶奶曾向刘霞诉苦,去年孙子找她要零花钱,不给就威胁卖掉她的摩托车。
在被警察送去启航学校前,周希军已经辍学在家近一个月。周希军的初中同学兼好友王凯告诉本刊,周希军从小学习普通,在镇上念初中时,成绩常年徘徊在倒数一二。他是最让老师头疼的学生,坐在倒数第一排垃圾桶旁边的他,上课经常跑到第一排,蹲在过道上跟朋友讲话。“抽烟、喝酒、吃槟榔、打架、纹身、谈恋爱,样样都沾。”王凯说,周希军外号“老鼠”,性格有些张狂,“见到谁不爽就要打别人”。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是因打架结识的,只是,清瘦的他常是被打的一方。
在刘霞印象里,周希军读六年级时,就已经“有混的苗头”。那时,只有11岁的周希军常常骑着摩托车,四五个人一起,油门加满,声音炸响。刘霞58岁,儿子出生于1991年。她告诉本刊,她儿子那一辈,村里就有十几个混混少年,跟出事前的周希军很像,染着黄的、粉的头发,混迹网吧,后来有三人因吸毒贩毒被判刑。刘霞说,村民文化程度不高,对孩子从小纵容,长大后发现问题,就用棍棒和禁闭应对,但已经不管用。像周希军一样骑摩托车到处逛的,刘霞在村里看到了四五伙。每隔一段时间她就听说,因为小偷小摸,某某家的孩子被抓了,某某家的孩子又被警察带走了。
刘霞说,周希军父母很重视教育,大女儿距离公办高中分数线差十几分,父母花2万供她读私立学校,周希军小学也上过2年补习班,一个武术班就花了1万元。但忙碌的他们,并没有关注到周希军的变化。直到去年下半年,周希军开始厌学,他们才想办法管教孩子。刘霞看到,张梅夫妇每天把儿子带去工厂上班,希望他体会赚钱的不易,但十来天后他就不再去。他们还曾送他去衡阳一所文武学校,他在里面待了一天,就翻墙跑了出来。周希军的一位朋友说,寒假时家里得知他抽烟,不敢给他钱,他就跟人去“扒车门”,最后被抓。
 浦口镇的街头(陈银霞 摄)
浦口镇的街头(陈银霞 摄)
在专门学校调研时,苏明月接触过不少越轨少年。她告诉本刊,当孩子无法在家庭和学校建立亲密关系时,他们就会投入帮派团伙,在同龄帮伙的交往中获得存在感、依恋感甚至成就感。在这个圈子里,金钱是维护友谊的方式。在王凯印象里,周希军“有钱、有摩托车、有苹果手机”,每天的零花钱10-20元,是其他同学的两倍。他抽18元的利群香烟,打每小时25元的台球,吃每包十几元至几十元不等的槟榔。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提及,对待朋友他十分大方,经常请朋友吃零食、喝饮料。朋友不清楚他父母的工作,但都相信他家境富裕。
不过,一旦父母切断了金钱来源,一切就会往着不受控的方向发展。有朋友曾亲眼看见周希军使用手机赌博,有时也会骗钱。周希军和朋友以合伙购买摩托车的名义,骗过一个学生几百块钱。进入启航学校前,他开始跟人去“扒车门”。魏薇说,“扒车门”就是去忘记关车门的车上偷盗。参与者分工明确,一人拉车门和放哨,两人迅速坐进车里,关好车门,在驾驶室快速翻找。魏薇说自己最多一次,她拿了2000元,还有三四包烟。

从启航学校出来后,魏薇并没有回家。她从小由奶奶照顾长大,父母在周边县市打工,两三个月回家一次。她跟父亲上次讲话,还是一周前,父亲对她很不满,威胁“要打死她”。魏薇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她每天睡到中午起床,然后跟同伴出去玩,一直到凌晨才结束一天。她也想过去找工作,但总觉得不顺心——只有餐馆、理发店招收16岁的未成年人。她和朋友跑了几家理发店,店里要求学徒必须缴纳2000元学费,他们交不起;餐馆要求他们提供健康证,办证要80元,钱也不够。后来,她去了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又觉得无聊赚钱慢,干了半天就跑了。本刊记者见她的那天,她口袋里只有33元钱,她买了一包20元的烟,又买了5块钱的泡面,开始跟朋友打麻将,输了20元。她并不着急,说第二天可以回家找奶奶要零花钱。
(应受访者要求,除周希军、苏明月、唐稷尧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排版:初初 / 审核:小风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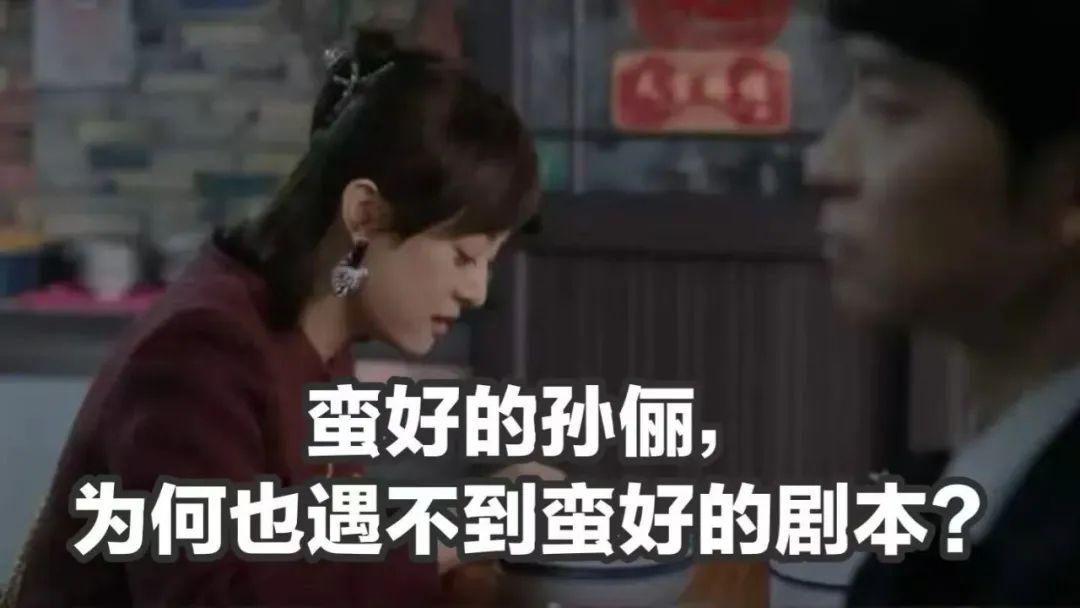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5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5976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