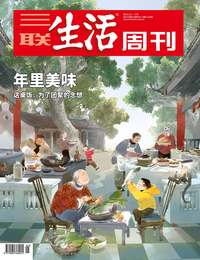米粉里的记忆与乡愁
作者:王珊
2021-01-28·阅读时长18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9489个字,产生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日思夜想的米粉
去桂林写米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味蕾的记忆。2014年,我刚毕业不久,去桂林出了一趟差。如今已经想不起住在哪个酒店了,只记得附近有一家米粉店:店铺面不大,大概四五个平方米,靠墙摆着一溜长桌、几张凳子,来吃粉的人一个挨着一个。人太多,很多人就端着米粉站在店门口吃,有的还会晃悠到马路对面,与街坊聊聊天。我记得自己吃的是一碗干拌粉,说是碗,其实只是一个不锈钢的盘子。在我的印象中,食客对米粉是有很大的操作权的——当掌厨师傅将加了卤水和牛肉、锅烧的粉递过来以后,食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加上酸笋、酸豆角、辣椒等等。这些加料摆在店里的公共区域,多达七八种。
这些关于桂林米粉的碎片影像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其实已经想不出粉的味道,但记忆暗示我,那碗粉的味道是非常美妙的,以至于我总是心心念念想着再回桂林吃一次粉。比起我这种作为过路者突然萌生的兴趣,白先勇对桂林米粉的牵挂是更深的。白先勇是桂林人,离开桂林时,白先勇只有6岁,他却清清楚楚地记得鹦鹉山、斗鸡山、雉山、骆驼山、马鞍山、风洞山……更记得花桥桥头的许多米粉店,米粉又细滑又柔韧,“从此一辈子没忘过”。他说小孩子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能把看到的东西拍下来,这些图像都在心里存了档。上世纪90年代,这些童年的记忆和乡愁被白先勇写进了短篇小说《花桥荣记》里。这里需要指出一下:小说里的花桥荣记是一家米粉店。
胃里的乡愁依旧难以抵挡。每次回到桂林,白先勇三餐都要吃米粉,一餐能吃得下五两。这个五两可不是我们理解的计量方式里的“五两”。在桂林,一斤大米,在经历加水浸泡、磨浆、滤干、和团、压榨、煮等多个工序后,能够生产出2.6斤的米粉。所以白先勇嘴中说的“五两粉”其实是1.3斤米粉,这还没有算上与米粉相配的牛肉、锅烧等。尽管如此,白先勇却说再多也吃不饱,因为肚子里的乡愁太多。

老盐街米粉店,小姑娘的碗里是二两米粉,胃口不小
一碗米粉也是广西文史学者林志捷日思夜想的。他出生于1963年,离开家乡已有20年,后来定居在北京,他在电脑上打开桂林市的地图,给我讲桂林的米粉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因为漓江的水质好。漓江发源于兴安县境内的猫儿山,从源头向南,江水进入灵川县境后,200来公里水流经过的都是喀斯特峰林地貌,水质偏碱性。而兴安县北部属湘江、长江水系,沿岸多为黏土岭,水质比漓江酸性强。桂林人相信,桂林的米粉好吃,完全得力于这一段喀斯特峰林地貌的水质,离开桂林百八十里,就是从桂林请的师傅,也做不出像桂林的米粉了。
林志捷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米粉,都是在桂林的亲戚朋友们给寄来的。他给我煮了一碗粉。这碗粉的来源听起来有些不太正宗,是一个桂林的老友在广州做的米粉,卤水和料包都是配好的,算是方便食品,“他也是思念家里米粉的味道,所以就自己琢磨着做,口味上算是80%接近桂林的味道了”。他边煮粉边跟我讲他自己在厨房的各种琢磨,其中一个是,他自己买了江西的干米粉,在水里泡上一晚上,第二天用热水冒一下,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桂林米粉的味道。不过,接近的言外之意是,“还是差了些”。
他总是想起在家乡吃粉的各种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地点在桂林西城路口的夜市。林志捷说,每天傍晚夜色将要袭来之前,无论酷暑严寒,夜市东边的第一个摊位都会有上百人排队。这是一家卖卤菜粉的小摊。林志捷现在都记得老板的模样:50多岁,五短身材,塌眼皮厚嘴唇,酒糟鼻总是油腻腻的,像一个浸透了辣椒水的大号老蒜头。也因此,这家小摊被叫作“红鼻子米粉铺”。比长相更让人印象犹深的是师傅手里的一把大板刀,刀背厚实如书脊,却能将卤肉片切得薄如蝉翼,肚丝细得都能钓鱼。
排到的人冲着老板喊一句:“一过二,米粉。”这是桂林人的默契——“过”在桂林话里是“个”的意思,即要二两米粉的意思。食客们最害怕的是还没轮到自己喊出来,红鼻子师傅将菜刀重重往砧板上一放,这意味着当日的米粉已经售罄,大家只好不情不愿地作鸟兽状散。“他每日只卖10箱米粉。”林志捷每次回桂林,只要放了行李,就会跑到街边吃上一碗粉,店总是随机挑的。可能是一家知名的店面,也可能是街头巷尾一家平平常常的小店。“桂林老城区就没有不正宗的米粉,只是各家调味有差别,各人有各人的喜好。”就在前两天,他刚刚去了一家门头特别不起眼的小店,他说:“三鲜汤粉粉肠嫩、腰花脆、瘦肉鲜,吃得几爽神!”
文章作者


王珊
发表文章155篇 获得6个推荐 粉丝838人
哈哈,天下天鹅一样白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