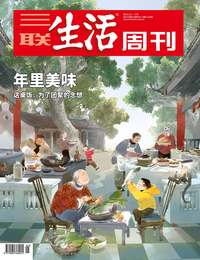沿东海,一路向南
作者:黑麦
2021-01-29·阅读时长3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5920个字,产生1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插图 阿梗)
本文摄影/于楚众
这几年,我不断翻看着张新民和朱家麟撰写的和东海有关的文章,他们的文字生动,可我仍旧缺乏感性的认知,无法想象某种海产品的消亡会对某个地区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也无法真切了解到某地的人对一种鱼类为什么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寄托。带着种种疑问,我买了张前往沈家门的机票,向东海进发了。
这是一次无关地理兴衰的探访,我试图将更多的目光移到海上。东海是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的最东沿——从长江出海口以南,一直到福建东山岛最南端的澳角村,这片70余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是中国海鲜的主产地。我们常说的“东南沿海地区”指的便是浙江和福建,前者“七山二水一分田”,后者“八山一水一分田”,靠山吃海,大致说的就是如此一番景象。这条海岸线远比我想象中的漫长,到达沈家门之后,我们从舟山出发沿滨海高速一路向南,原本预计10天的路程开了15天,每踩一次油门,心中都充满着莫名的兴奋。
沿途经过中国四大渔港中的两个:位于舟山本岛东南侧的沈家门渔港,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渔港;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的石浦中心渔港,它是东南沿海著名的避风良港,可泊万艘渔船。这里曾经的鱼类资源极其丰富。1975年时,渔业调查船从石浦渔港出发,开不出几十海里,一网下去就能捕获鲐鱼、金枪鱼、马面鱼、竹荚鱼、蓝圆鲹等十几种鱼类。45年间,渔民赖以生存的海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渔民经历了从“东海无鱼”到“东海护鱼”的过程。2021年是东海伏季休渔的第27个年头,渔业在困境之下艰难恢复。即便如此,岸上仍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从渔港到市场,从餐厅到餐桌,依然有大量的海鲜供给。当你站在东海沿线的时候,餐桌上的海鲜便产生了更丰富的味道。

在海鲜市场买梭子蟹的顾客
舟山
北京目前每天只有四架飞机飞往沈家门,大多是在晚上,飞过上海的时候,遭遇到强烈的气流,机舱外一片漆黑,下面应该是海,偶尔能看到几个晃动的光点,大概是被海浪托起又扔下的渔船。飞机穿过云层,雨水猛烈地拍打着舷窗,直到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山丘中间的跑道上。
出机场,鼻腔果然被湿气包裹住了,那个咸腥味,像是一种对味觉的洗礼。酒店也充满了咸味,被褥潮湿,下水道里反出一股幽幽的腥。入住没一会儿,船员老林打来了电话,“准备出发”。他说话有很重的温岭口音,为了得到准确信息,我问道:“是现在吗?”“是。”老林说得很清楚,随即他挂上了电话。
凌晨1点,我乘车来到岛东南侧的沈家门渔港,登记完各种手续,我来到了4号码头。远处,靠港的渔船纷纷卸货,装上补给,急匆匆地在狭窄的港内调头,再次冲入大海。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闯入者,因为这里极少有游客打扮的人出现,大多数人穿着胶皮制的工作服。不过,我和他们一样清楚,深夜,潮水上涨,正是潜入大海的最好时机,再晚了潮就退了。
要在黑漆漆的海上物色到一条摆渡船并非易事,顺着突突突的声音,依稀看到了这些小船的聚集地,我走上前去,向他们呼喊、招手。不知是手机还是电筒的亮光,向我挥动了一下,突突声越来越大,有船来了。
因为不时有渔船靠港卸货,岸边的浪此起彼伏。我趁船头下沉,一个箭步跳了上去,等我站住再回头时,摆渡小船已经开始离岸。接送上船,10元一位,水手、工人、船长一律10元,我掏出手机扫了付款码,开船的示意我坐稳扶好,在这条三人宽的小船里,我是他唯一的船客。
大船就好上很多,接应我的林奶春师傅伸出一条黝黑的胳膊,扽着我的书包带一把给我拽上渔船。林师傅今年40来岁,出海快30年了,他之前也是船老大(船长),前年刚卖了自己的渔船,又闲不住,回来当起了水手。这条船的船老大叫毛小三,和老林及另外7个船员都是从温岭的同一个村子里出来打拼的,有几位在这条船上干了18年,他们自称是与海鲜交手的第一批人。

在浙江,海鲜自选台就是“菜单”。图为台州新荣记餐厅,厨师拿起一条舟山带鱼
很快,我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语言不通。船员之间只说温岭话,他们中只有三四个人会说普通话——还不好意思开口,唯一的突破口是那个湖北籍船员老颜。他对我说,现在他们说的话他基本能听懂一半,我问他在船上待多久了,他回答,10年。没有一种语言叫浙江话,在浙江地区,隔一座山,就是另一种方言,方言之间差别很大,在舟山的海上,漂浮着各种方言,这是只通行于每条船上的秘密语言,也是水手默契协作的基础。
老颜带我在甲板上转了转,所有的木板都刻有编号,且都能掀开,每块木板下的功能大不相同,有普通暗格,还有低温隔断,有专门存放活鱼活蟹的水池,在整个隔断的最下层,是一个巨大的冷冻室。走进船舱就会看到水手们休息的“房间”,其实就是个横向开合的“柜子”,里面有被褥和充电插头。“风浪太大的时候,必须拉上柜门平躺,不然就滚出去了。”老颜指了指自己的那间说,“你累了就在我这里休息,反正有你在我们不会离岸太久的。”
船舱的二楼是驾驶舱,船长、大副也住在这层,他们的卧室——如果这也可以叫卧室的话——大了一些,还配了卫生间,可以洗澡,船长的那间多了张写字台,大概是算账用的。老林一直在开船,很认真的样子,深夜的海上漆黑一片,他不断观瞧着GPS定位和雷达。
约莫两三个小时后,大概是停船了,船员们呼啦啦地走出船舱,开始下网。盘在甲板上的渔网像是一个巨大的线团,只要递到水面,就像有人接应一样,被一节节地送进海里。船大概是抛了锚,在小浪上规律地起伏。
毛老大的表情有点凝重,他只说了句“鱼少”,便走开了。我问老林,为什么我们要停在鱼少的地方,老林说:“是这几年鱼都不多。”没过多久,海上起风了,浪跟着变大,不时有海水拍打到甲板上,顺着船的夹缝再流出船外。大副看我有点晕船,一个劲地笑,他说:“这才7级风!”我问他,这船能抗多少级,不知道他是在讲笑,还是认真地回答:“17级。”大副说:“现在出海早就不像以前那么危险了,有气象预报、巡逻船,还有卫星电话和定位,要是有预警,渔港都不让你出船。”他继续说道:“危险都是人为的,有人开船玩手机,撞啦。”

在沈家门渔港,船员拎着刚捕捞上来的比目鱼
船摇了几个小时后,终于稳定了,等我再睁眼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我终于看清了水手们的样子。不知道船是不是还在原地,海风一个劲地吹,像是要给我们吹回岸边似的。这是船上最清闲的一段时间,老林吃了些土豆炒年糕,在甲板上踱步,我和船员们打了两把扑克,几个人之中只有我显得焦急,大概是因为我忙于看底牌,确实,我也想看看渔网里的“底牌”。
上午10点刚过,毛老大冲着水手们喊了一嗓子,我没听懂,可船员们听懂了,到了收网的时间。马达声轰轰作响,渔网卷着水草和一些垃圾最先浮上海面,随后我感到了船的侧倾,那渔网显得很沉的样子。最先看到的是一些小鱼和螃蟹,随后拉上来的是一坨一坨的,说不清那里有多少种鱼,我猜二三十种是有的。捕鱼的场面是极为壮观的,网一散开,甲板上满是鱼虾蟹,船员们不知什么时候都换好了胶鞋,在海鲜中走来走去,被清空的渔网再次被送回海里,周而复始。
清点货物,需要眼疾手快,渔民们靠多年的经验练就这种本领,他们在甲板上支起桌子,每个水手身边四五个塑料网筐,被拾起的海鲜,就此分类。我依稀辨认着这些海货的名字,鱿鱼、墨鱼、剥皮鱼、泽鱼、鳡鱼、马鲛、马鲛虎、梭子蟹、石斑鱼、带鱼……还有很多不知道名字的鱼。毛老大低头看了看这些海货,像是在视察,又冲水手们喊了几句,于是大家加快速度,有人从冷库里推出十几箱碎冰。
鱼躺在冰上,立刻停止了挣扎,虾也一样,不再扭动,沉沉地睡去,一箱箱的海鲜被送回冷冻室或是冷藏室,活蟹被塞进圆形的塑料筐内,扔到有海水的格子里,和几条活石斑鱼成了邻居……老颜拿起一条黄花鱼和一条东海金枪鱼笑得合不拢嘴,他说好久没见过这么大的黄鱼了,“这鱼有两斤”。我问他,咱们中午能吃这鱼吗?他并没意识到我在开玩笑,收起了笑容,继续分拣。
文章作者


黑麦
发表文章231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2330人
沉迷于对抗中年危机的美食作家,对groove着迷的音乐编辑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