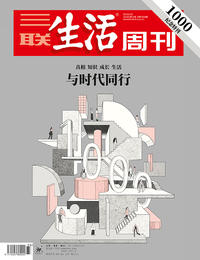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作者:徐菁菁
2018-08-16·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912个字,产生5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走出去
第聂伯河从北至南奔向黑海,将基辅一分为二。在河右岸,基辅人沿着河岸倚山建立了一连串的公园。那个刚下过一夜雨雪的初冬早晨,马林斯基公园里,斑斓的树叶铺天盖地。第聂伯河的氤氲从枝枝蔓蔓的树丛间闪现出来。城市笼罩在灰色的雾气里,河水倒映着深深浅浅的天空。这是2011年11月,基辅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深刻画面。那时,《三联生活周刊》正在策划苏联解体20周年的封面报道,几位同事被分别派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做实地走访。面对这片陌生的土地,我欣喜而又忐忑。那是我第一次出国采访。
2009年,我毕业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机缘巧合,就在我刚要入职的时候,老主编朱伟决定开辟一个新的“观察”栏目,每周为读者提供2~4个国际时事观察分析,每个篇幅1页。主编对我们的要求是尽可能地采访国际专家、学者,对政治事件和话题提供简短但信息含量密集的分析。这份工作做久了,我们都有些倦怠:由于题材和体例的限制,“观察”栏目的写作很难展现细节,体现个性。而且,我们与那些国际时政中提到的国家和要人远隔千山万水,我们完全需要通过既有的材料和分析家的眼光去认识他们。这种隔膜感时常令人感到沮丧。
回头来看,这是主编的“一盘大棋”。2009年之前,国际报道并不是《周刊》一个重要的报道门类。2008年10月,《周刊》制作了一期冰岛金融危机的“封面故事”,那是那一年唯一的国际话题“封面故事”。2007年7月,国际话题“封面”的独苗是西班牙文化年寻踪。再往前,2006年,周刊的“国际封面”为零。但从2009年开始,《周刊》对世界的关注陡然增加。随着钓鱼岛、南海等问题的升温,围绕中国利益展开的国际关系分析屡次登上“封面”。关注《周刊》的读者不难发现,近些年,国际话题的“封面”变得越来越多。现在看来,不起眼的“观察”是《周刊》的一方苗圃和试验田。每周2个国际问题分析的写作让我得以在这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获得迅速的知识积累,我们逐渐把国际时事从1页的小文章,扩展到了4~6页的详细报道。
2011年可以说是一个转变之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穆巴拉克下台;欧美介入利比亚局势,卡扎菲殒命;匿藏多年的本·拉登最终被击毙;欧债危机爆发。所有这些事件,《周刊》都做出了迅速反应,制作了详细的封面报道。另一种趋势也在显山露水。那时候,绝大多数的报道还是在“隔岸观火”:主要依靠记者对资料大量搜集、处理和逻辑建构来完成文章。我们相信自己的这种能力,但也对此怀有警惕:在远离第一现场和核心人物的情况下,文章是否缺乏真正鲜活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在被二手资料牵着鼻子走?我们有没有可能提出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和问题?
2011年11月,我们兵分几路奔赴前苏联的土地,大概就被赋予回应这些问题的期望。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全新的考验:出发的时候,我并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作文命题。签证只给了我10天时间,没有人能告诉我选择写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观察一个国家,应该去找哪些人聊聊。我像是一个素描新手,面对一桌子静物,全然不知从何下手。

在乌克兰,陌生国度的风物、气息和它鲜活的人民给我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基辅,我走过1.5公里长的克利斯卡提克大道,想象1941年,德军占领基辅,苏联在400公里外用无线电引爆了炸药,这里的300多栋建筑灰飞烟灭;2004年冬天,它又成为“橙色革命”的风暴中心,曾有100万人挥舞着橙色旗帜,涌入这里支持总统候选人尤先科。我走遍了城中的教堂、修道院,听闻宗教影响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变化。我拜访了女记者奥克萨娜·法纳利一家,普通乌克兰家庭的生活在20年变迁中的种种细节令我动容。我还去探望了83岁的克劳迪娅·库德里亚肖娃,她是苏联时期乌克兰最重要的宣传画画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在节日里,她的作品被制成4米高的巨型海报,和领袖肖像一道安放在基辅的“十月革命”广场上。2011年的夏天,她刚举办过一次展览,那是20年来库德里亚肖娃第一次公开展出自己的作品。然而不幸的是,我在这些信息的狂流中迷失了。
从乌克兰回来,我写了两篇文章。集中于基辅见闻的一篇勉强付梓,另一篇被主编毙掉了,那是我在《周刊》第一次遭遇毙稿。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东西乌克兰陷入对峙。回想起3年前的那篇毙稿,我惋惜不已。在被毙掉的稿子里,我试图讨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和发现。我注意到了这个年轻民族国家的问题:新一代和老一代对国家的独立道路持有不同的看法;东西乌克兰之间在文化、历史、经济上的裂痕甚至比代际的裂痕更大。在西部重镇利沃夫,老派又时髦的利沃夫人走在如布拉格一般的古城里;政府积极修复着老城,设立英文路标,努力吸引来自西欧的游客;在这里的报纸上,是否应当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依然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甚至会引发暴力冲突的话题。而在东部的哈尔科夫,我见识了一座没落的工业重镇。这里的时间似乎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停滞。地铁依然以苏维埃站、无产阶级站、苏维埃红军站、劳动英雄站命名;市郊区延绵着成片的寂静厂房和陈旧的工厂宿舍,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庄严肃穆的大楼上还可见苏联共产党的标志。独立20年,哈尔科夫失去了苏联时代享有的交通枢纽地位,其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未完成转型,人们依旧认为,俄罗斯才是未来的机会所在。
文章作者


徐菁菁
发表文章143篇 获得14个推荐 粉丝1762人
《三联生活周刊》资深记者。写字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