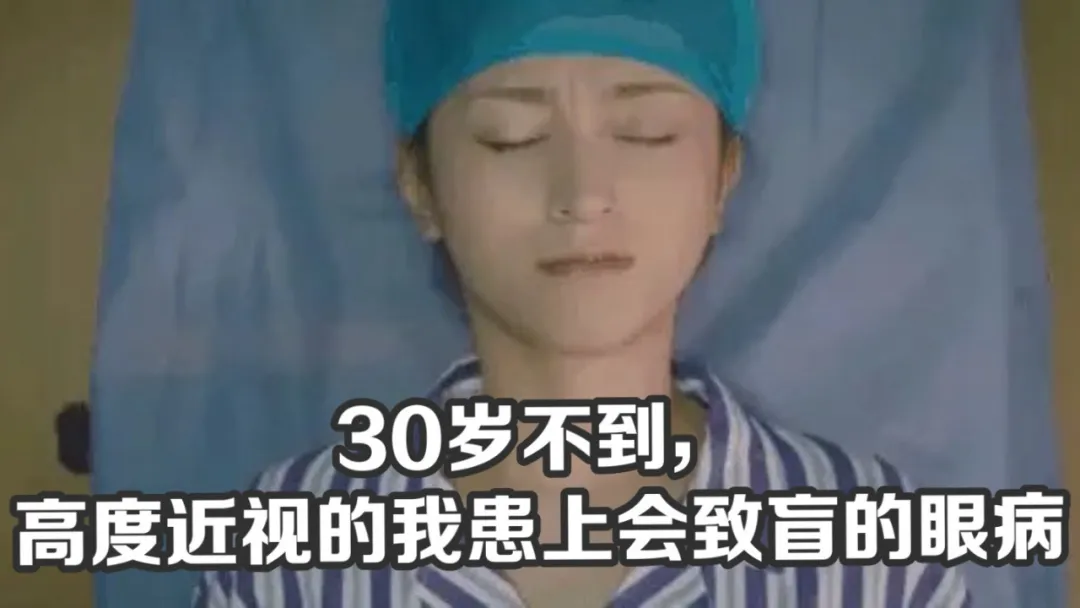被美国家庭收养14年后回国寻亲:“我只想着解决生活抛来的问题”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27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苏伢子”最近找到了他的亲人,也找到了他的真名“吴苏成”。“苏伢子”是他的小名。
2002年,6岁的他从江西被邻居带到广州卖花。之后警察将他解救送进广州一家福利院,他的童年在此度过。9年后,他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长大成人。由于语言不通,他和养父母的感情在日积月累的误会中逐渐生出罅隙,考上大学独立生活之后,又因为助学贷款的压力过着拮据的生活。
2024年,在一场重病之后,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一直向往亲情的苏伢子开始寻亲。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今年3月,他回国与亲人相认,在不富裕的家里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接受本刊采访时,他的表达一直很平静,并没有因为过去的苦难抱怨生活,他觉得那都是命运的安排,很多时候他没想着苦,只想着解决生活抛来的问题。
以下是他的讲述:
编辑|王珊
拐卖
3月23日,我和我失散23年的亲人相认了。那天我从醒来就很兴奋,但坐上回家的车,就萌生了另外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既想笑,又想哭。在村口的祠堂,政府为我们办了一场认亲仪式,现场有非常多人,各种鞭炮的声音响了一路。
见到妈妈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止不住,她哭着喊我的小名“苏伢子”,我马上抱住她,放声大哭。在祠堂里,一位记者提议我叫一声“妈妈”,我叫了好几声,妈妈应了好几声。我太久没有喊过“妈妈”了,我想告诉妈妈她的小儿子回来了,现在就在她身边。
 苏伢子和生母(图源凤凰网纪录片《旅途》)
苏伢子和生母(图源凤凰网纪录片《旅途》)
我最近才知道我的名字叫“吴苏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用“越发刚”这个名字生活——是我被送到福利院时,福利院给我起的。进福利院前,我只记得妈妈用方言叫我“苏伢子”,我只记得三个音,不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
我是在2002年被拐卖的。当时我才6岁。村里的一个男人跟我父母谈话,说可以带你们的孩子去广州卖花,吃饱饭有更好的生活,还能学一些技巧。我家那时很穷,父母都在家种田,休闲时妈妈编织鞭炮售卖,爸爸开拖拉机,挣点小钱。当时我们镇的经济都比较困难,孩子跟着出去卖花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附近很多邻居的小孩也都出去卖过花。我和比我大一岁半的哥哥就跟他走了。下了火车,我们来到了一个气候很不同的地方。
卖花有“老板”,一个“老板”带领5-8个孩子。我们白天睡觉,晚上卖花,起床之后,老板会给我们一碗面吃。主要卖玫瑰花,红色和白色,对象是情侣,他们有买玫瑰的意愿,也容易对孩子产生怜悯。我记得很多次老板把我推到一对情侣面前,我就把花递给他们。我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每隔几天就会换一个地方,有时候是在谁的家里,有时候是在某个公寓里。听父亲说,我们在广州卖花,每个月有10多块钱的工钱。
我是在来广州一两周之后走失的。我太小了,没有这段记忆。听哥哥说,当天卖花的地方人很多,挤来挤去的,我跟在哥哥后面,不到10秒钟,哥哥再转头,我就不见了。这之后,我遇见了第二个卖花的“老板”,我对他的记忆不多,他比较虐待孩子。要是没卖出去多少的话,他们会把我的衣服脱光,绑在公园里的健身器材上,用铁衣架折成鞭子抽,疼得我大哭;还会用小刀划伤我的脚背,让我流几滴血。这样我白天就会拼命地卖花。
过了一两周,正巧有警察巡逻,看到我手上捧着很多玫瑰花,他立马反应过来,抱起我,我被解救了。但我当时太小,不识字,不记得家人的名字,也说不出家在什么地方,警察也找不到。我被送到了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福利院给我取名“越发刚”,因为我是在越秀区被找到的,我特别瘦,特别虚弱,福利院希望我越来越刚强、强壮。
 福利院时期的苏伢子(图源凤凰网)
福利院时期的苏伢子(图源凤凰网)
我在福利院度过了9年,福利院比在外面卖花安全,能睡好觉了,每天都有荤素搭配的三顿饭吃。我还在福利院的教育系统上了学,认识了很多小伙伴,现在想来拥有挺多快乐时光。那时候下午四点半左右放学,大家一起玩,小孩喜欢拉帮结派地打闹,我属于比较调皮的,在我们那个团体里不知怎么成了“老大”,别的小伙伴受了欺负,都会找我出面。
去美国
其实在福利院时,我就一直特别想回家。我还逃跑过一次。一天早上10点半左右,趁着阿姨打开大门送东西时,我和另一个想逃跑回家的小伙伴一起溜了出去。但我们不知道回家的路,一直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走,后来福利院找到了我们。
2011年3月,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要去美国了。福利院基本每年都有孩子被海外家庭收养。那年我已经15岁,但我不知道去美国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美国在哪里,也不知道那里的人怎么生活,听说要去美国心里特别害怕。
一个月后,我见到了美国的养母。她来中国和我相处了两个星期。她看起来高贵漂亮,待人温和。对于跟她去美国,我开始有些期待。我没有刻意去讨好她,只是认真自然地和她相处,我们互相都比较尊重对方,客客气气的。我那时候才上四年级,英语是三年级学开始学的,只学了字母,完全听不懂。养母也不会讲中文,她带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每次想跟我讲话的时候就打开电脑,用谷歌翻译。她非常细心地照顾我,每一餐都会问我想吃什么,带我去了广州的一个动物园,拍了很多照片,还去了另外一些景区。
养父母家在纽约州水牛城的一个小镇上,是一个挺漂亮的小房子,有三层,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前面有片小草地,后面有个小院子,家里是木制装修风格。养父是机械工程师,养母在家带孩子,他们都是50来岁。我是他们家里的第九个孩子,也是他们收养的第四个孩子。他们自己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比较注重隐私,我没有特意问过另外三个被收养的女孩来自哪里,听养父母提过,其中有一两个来自海地。我是家里唯一一个中国孩子,也是家里唯一不会讲英语的人。
 读书时期的苏伢子
读书时期的苏伢子
我到时,家里加上我一共住了八个人,因为房间不够,养父母就把地下室改造成了卧室。地下室大概三四十平米,刷了漆,装了灯,放了一张床,一个沙发,一个桌子,一把椅子,用竹子编的一个储物箱,还有一个衣柜,装修还挺好的。也有不好的地方。地下室很冷,很潮湿,也很黑。我比较怕黑,有时候晚上开着灯睡,但养父母会提醒我关灯。我不会说英语,就没有跟他们解释说我是怕黑才开灯,也怕给他们造成麻烦。我晚上经常睡不着。
我跟养家的人交流不太多。很长一段时间,我需要用谷歌翻译来跟家人交流,但我不可能总是捧着电脑,更多的时候只能靠猜,通过对方的语气、表情、手势,有时候能猜对。吃得也不是很习惯,都是美式的食物,比如汉堡、鸡块、牛排,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西餐。不过我不挑食。我跟几个兄弟姐妹的关系还不错,孩子间的交流不依赖语言,我们年龄相差不太大,平时会一起看电视,在家里打篮球、踢足球,有时也会一起逛街,参加他们学校的活动。
养父母对我挺好的,为我考虑了很多。看到好看的、适合我的衣服,他们会买给我。也送我去上了学。考虑到我不会说英语,他们为我挑选了一所Chapter School,这类学校由州政府立法通过,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规定约束,学校不区分初高中和年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申请课程,我的课也是养父母帮忙选的。班级的人数也不多,每个班不到20名学生,老师有精力照顾到每个学生。可以说,养父母的收养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觉得很满足。
孤独
我是在到美国差不多两年后开始和养父母变得疏远的,我觉得他们对我越来越严厉、冷漠。现在看来,还是语言不畅。
我生活和学习有一个很大的阻碍,是我的眼睛。去广州前,我捡爸爸扔在地上的烟头玩,不小心引爆了炮竹。我被炸倒在地,右眼几乎瞎了,只有一点光感,左眼高度近视,视力只有0.12(相当于500-600度近视)。所以Chapter School的老师一开始只让我读一些特别简单的书,三岁小孩子读的那种,几个月后我慢慢能看懂这些书,但不怎么能读出来。半年后,我学会了简单的英语写作,还是说不了英语,发音不标准,语法也不对,别人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两年半之后,我才能听懂比较复杂的句子。
我能想到一件小事,也是我刚到美国不久时发生的。在家里,养母的儿子喜欢不穿鞋走路,有一次他走在木地板上,不小心踩到一块玻璃,割伤了脚。我正在看电视,看到一个好笑的画面,发出笑声。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养母跑到客厅对我说,那件事情不好笑,就走了。我想解释,但我不会说英语。等养母过了气头,事情就过去了,我们又回归到自然相处的状态。
仔细回想起来,这样的事情后来其实不断在发生,很多小事我解释不清楚,养父母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多多少少造成一些误会。可能在任何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这样,小误会如果不解释清楚,日积月累总是会影响感情。英语好些之后,我有几次问过他们为什么不高兴,他们也会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好,我向他们解释,他们有时候并不认可我的说法,说我在找借口,或是想推卸责任,所以后来我解释得越来越少。
也是因为眼睛的问题,我很少出家门,不知道家附近是什么样子。直到2013年秋天上了高中,天气好时我放学会自己回家,才慢慢熟悉家附近的环境。我也很少和别的朋友玩。我的夜视能力很差,晚上基本不参加同学们的活动。走路经常碰到东西,比如进门的时候胳膊蹭到门边,看不见透明的玻璃,一头撞上。我生活起居的所有事情都是养父母安排,很多基本的生活体验我都没有。比如我不知道去哪里买菜,找到菜市场以后,我不知道那些菜是怎么卖的,因为有些没有价格标签,挑好菜我又不知道怎么付款。我还挺害怕别人投来的那种“怎么这么大了,连买菜付款都不会”的目光。
我后续的读书也很吃力。上高中以后,我要跟其他同学上一样的课,看一样的书,写一样的作业。虽然英语变好了,但我完全跟不上。我属于特别努力的,几乎没给自己留任何娱乐的时间。养父母没有和我聊过人生规划,上大学是我自己的决定。那时我认为,去自己想去的大学读书,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好大学意味着未来更有可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我们下午4点半左右放学,美国高中的作业不怎么多,我的同学们一般花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但我经常要做到6点,作业多的时候甚至会到9点。我做作业要用便携式放大镜:我既看不清书上的字,也看不清自己写了什么。
2017年,我考上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University at Buffalo),学电子工程。美国大学的学费挺贵的,4年总共需要12万美元。我自己申请了助学贷款,包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食堂费,还有购买额外的学习材料的费用。美国的家庭注重孩子的独立能力,孩子贷款上学的情况很普遍。我不再依赖父母,感受到一种自由,但自由的另一面是孤独。
 2017年,苏伢子考上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2017年,苏伢子考上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我找了几份工作。我参加过学校内部的志愿者活动,带领高中生参观大学,给他们讲解,工资是每小时15美元。我还做了另外一份相对长期的工作,是在校外一个专门为盲人提供工作的地方找到的,工作内容是根据客户的需要把商品装进箱子,寄出去。那份工作的工资是每小时10美元多一点,一天不到100美元,寒暑假我是全职,上学期间每隔一天去半天。大三的暑假我又去了一个电子元器件组装公司工作,每小时不到15美元。我做这些工作主要的目的是挣自己的生活费。这也是我很渴望得到的一种社会经验。
大学期间,我的生活很节俭,从来不买不需要的东西,吃的最多的是泡面。我在食堂卡里充的钱不多,不够我每天吃一次。我也没那么多时间自己做饭,最开始只会把各种蔬菜和肉放在一个锅里乱炖,后来学了一些炒和煎的技能,现在会煎蛋、煮蛋、炒蛋、煎牛排。大三我就和同学一起在校外租公寓了,是为了省钱。如果住宿舍,一学期至少需要贷款4000美元,住公寓每个月不到1000美元,能省下好几千美元。
我经常换公寓,主要是因为贵,我总想找更便宜的。也因为住不习惯,没有家的感觉,住哪里都不安心。美国的公寓不大,不到20平米,装修不错,里面是空的,床、沙发、桌子、椅子、厨具,生活用的一切都要自己买。那些我都不想买,一方面是舍不得花钱,另一方面搬家是个大问题,我眼睛不好,没有车,也开不了,家具很难带走。有些大件家具就算不要了,也不能留在公寓,不清理的话,房东可能会把押金扣没。所以我只买了床垫,放在地上,二手的桌子和椅子,只要二三十美元,常用的杯子、厨具,搬家的时候能卖就卖,卖不掉就直接扔。
寻亲
2021年我毕业,找到一份汽车安全碰撞测试的工作。这份工作的月收入是3000多美元。除去租公寓的600-800美元,贷款和各种杂费,我每个月的生活费不到1000美元。所以工作后我的生活仍然十分节俭,坐2美元的公交都觉得贵,我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每天骑20分钟去公司。
工作之后,我似乎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生活了,但我有时会想:我的家到底在哪里,我的父母到底是谁,这个世界上有人真正在乎我吗?我的心里好像一直有个声音在对我说,你不能就这样安顿下来,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要行动起来,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找。这件事一直让我很焦虑,睡不安稳。这些年我的睡眠一直比较浅,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惊醒,也时常睡不着,所以熬夜。工作之后生活规律了一些,会好一点,有时候下班回到家六七点,直接在椅子上累得睡着,醒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了。
2024年8月,我得了病毒感染性心肌炎,医生给我动了手术,我在ICU里住了两周。病好之后,我的心脏不会影响我正常生活,但它变弱了,导致我不能做剧烈运动。我很害怕再次发生意外,再也见不到我的亲生父母。这场重病让我下定决心回国寻亲。
一个中国的朋友向我推荐了“宝贝回家”网站。我把我记得的信息全都登记了:我家在一个山坡上,是个土房子,后山有个茶树林,还有一些田地,小时候我经常跑到山里采野果子,赤脚在田里玩耍。妈妈喊我“苏伢子”,我的眼睛在很小的时候被鞭炮炸伤……几天之后,“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联系我,让我采血寄回国,让公安部门做祖籍分析。后来我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说,他们通过妈妈编织炮竹售卖这一点,锁定了江西和湖南,又通过公安的祖籍分析确定是江西的吴氏家族。
恰好一位志愿者参加江西萍乡村民的家宴时,聊到我寻亲的事,有一个人说,这不是我家一个亲戚吗?志愿者给我发来爸爸妈妈和哥哥的照片,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谁啊,为什么给我发这张照片?再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长得都跟我很像。所以DNA比对的结果还没出来时,我就已经确信他们是我的家人了。我是在2月17日等到DNA比对结果的。找到亲人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我的灵魂有了归宿。
有了亲人的信息,我立刻着手办回国探亲的签证,更加努力地工作,每天加班1-2小时,每个周六都加班了,因为我想赚够回中国一个月的机票和生活费,不想让父母承担这些费用。回去前,“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跟我聊过家里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我的家境并不好,爸爸得了糖尿病、脑梗,还有很多其他的小毛病,妈妈有一些耳背。现在哥哥一个人养家。志愿者怕我承担不了家庭的压力,说得很严肃。我其实并不惊讶,也不介意,我有预感会是这种情况,只是觉得很感慨,这么多年父母过得不如意,挺想帮帮他们的。
我不担心父母不接纳我,我有预感,我们相互爱着。我听志愿者说,2月11日他们去我家走访时,跟我父母说可能找到我了,爸爸妈妈的神情立马伤感起来,妈妈就开始哭,爸爸也开始流眼泪,妈妈差一点跪在志愿者面前,恳求他们一定要把我带回家里。3月23日我回到老家,我家的土房子还在,几乎没什么变化,以前的床和一些老物件都还在,父母还睡在里面,他们可能习惯了住那里。边上建了一个新房,只有一层,两个卧室刷了白墙,还有一个客厅和一个卫生间。妈妈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
这段时间,我最开心的事就是陪着爸爸妈妈。他们的爱不宣之于口,但体现在很多小事上。像一日三餐,洗衣服,收拾房间,爸爸妈妈都想帮我做。哥哥和表姐也一直陪着我。在他们面前我可以任性,有时候会跟他们拌嘴,像变回了小孩子。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比如妈妈养了很多只鸡,它们都很可爱,不怕我。后山一片竹林,能挖到很多竹笋,饭桌上有几个菜是我们一起去家里的田里摘了做的,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去外面散步,能看到很美的晚霞。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的体验。
回国之后,我一下子得到了太多的爱。我在一个采访中提到眼睛的问题,网友们想到了陶勇医生,在抖音上给他发了很多私信和评论,没想到陶勇医生真的看见了,邀请我去北京免费做手术。我跟网友们素未谋面,但是他们却愿意帮助我,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感谢。术后我的左眼视力提升到了0.2,恢复好的话,可能达到0.3或更高,右眼的光感也更强了。以前距离五六米看人,我只能看到一个轮廓,现在能看清人脸了。我很感激陶勇医生,眼睛的问题是我人生的一块绊脚石,现在我觉得我又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陶勇医生和苏伢子的合影
陶勇医生和苏伢子的合影
等探亲的假期结束,我还得回美国。还完贷款,我希望申请回国上学或回国工作。客观来说,过去的23年我过得很苦,但我觉得都是天意的安排,我不抱怨,也不后悔。很多时候我都没想到苦,也没有责怪过任何人,只是想着解决我面对的困难,达成我的目标。再苦再累,那些日子我是真真实实过了的。我也遐想过没被拐走的生活,后来觉得无论是哪个结果,我都能接受,都是属于我的生活。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我现在更懂事了,也更加自由,还要继续往前走。

排版:布雷克 / 审核:小风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5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5974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