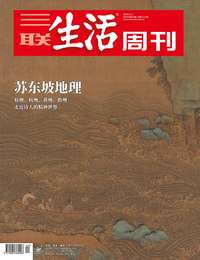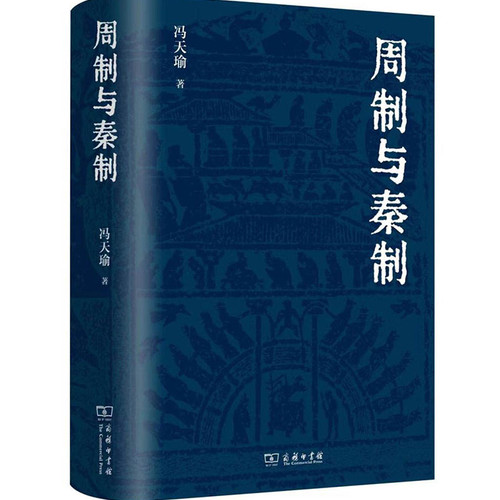被误解的章学诚
作者:维舟
2020-10-29·阅读时长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2440个字,产生1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章学诚
章学诚可能是遭受误解最多的历史学家之一。这位虽然相当自信但生前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文士,经历了100多年的长久冷落,到近代忽然暴得大名,被追认为新史学的先驱,因为他那句著名的“六经皆史”恰好迎合了“五四”时期打破传统、将经典降为史料的新理念。然而,这其实又是对他的双重误解,现在已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章学诚的本意既不是将六经贬为史料,更不反传统,相反,这个复古主义者念念不忘的是通过史学来上窥“王道”,以期复现“三代之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他看作是“历史学家”本身可能就是对他最大的误解,是一种现代学科分类的视角。如果回到他自己的著作脉络中去,就会发现,他其实自视为通才,“历史”对他而言所具有的意义也并不像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些过往事件的客观记录,甚至不仅仅是“学术”,还隐藏着“复归大道”的密钥,一如西汉大儒董仲舒、何休认为孔子著《春秋》是“为汉制法”,牵涉到天下秩序的重整。换言之,“六经皆史”的真实意义不仅是“史就是经”,而且是“史才是经”。
这种索隐式的解读有时近乎宗教性体验,也因此很难为人所理解。章学诚一再标举的“史意”,乍看简单,但究竟何意,却一直众说纷纭。章益国在《道公学私》一书中深入辨析章学诚的思维特点,分辨各家论说,认为“史意”的“意”并非“意义”,而是“意味”,因为章学诚所看重的是史著整体呈现的“美”——那不仅仅是文笔层面那种“表面的浮沫”,而是结构性的历史思想,是史家的性、情、才、气、识、功力等在史著中的凝结。这种“史意”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分领域、一个元素,而是作为“整体质”体现于整个历史研究之中,故而章学诚强调的不是理性思维下的严谨规范,而是要灵活、通脱、圆神,就像中国书画所说的“气韵生动”,乃是一种整体的“感觉”。
王家范也曾说过,中国文化重直觉,“即使是对民族历史的认知也离不了心灵的感悟”。问题在于,这种直觉的、整体性的“意味”是很难用语言说出来的,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有时看似高深莫测,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心通其意”无迹可寻,只能凭自己用心体会。章益国虽然专治章学诚思想多年,但就像他自己曾在讲座中公开说过的,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偏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本书中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章氏并不精于考据,凭感觉、‘想当然’的成分较多,很多地方只能说是‘智者的悬测’。”
相比起早先对章学诚的种种误解,这本旁征博引的著作确实更能深入地触达章学诚思想的奥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何以遭受如此多的曲解:因为他那种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很难纳入理性主导的现代学科格局。按张立文的观点,西方史学是“由求真而向外开出知识论”,中国史学是“由着意而向内开出心性论”,但现代史学的发展所遵循的正是前者的路径。除了传统的断裂之外,也因为整体的感知虽然看似高妙,却是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模糊“感觉”,有时甚至无异于难懂的谜语,无法加以理性地客体化分析研究。这样,一如本书所言,“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其间‘美’被失落了”。
文章作者


维舟
发表文章33篇 获得4个推荐 粉丝419人
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